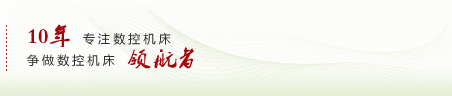直觀地看,這是對傳統(tǒng)經(jīng)典的“解讀”問題以及對其“效能”的寄望問題。
我們不難推斷,把《孔融讓梨》這個經(jīng)典故事列為課文的目的,落腳點就是為了使學生——肯定是“小”的學生——明白那個“讓”字,因而懂得“讓”,數(shù)控銑床中去踐行“讓”。現(xiàn)在你卻“不讓”,不是白學了嗎?在很多人的思維里,所謂經(jīng)典無非是一把標尺,量過去,合尺寸的就“對”,不合的就“錯”。不過,經(jīng)典本身未必有這樣的出發(fā)點。“香九齡,能溫席,孝于親,所當執(zhí)。融四歲,能讓梨,弟于長,宜先知。”《三字經(jīng)》里收入這兩個故事,是為了強調(diào)“首孝悌,次見聞”,后世如果當成標準答案,就跟科舉的遭遇差不多了。科舉到后來之所以備受詬病,在于對四書五經(jīng)的詮釋,概以朱熹的見解為標準;再弄出“破題、承題、起講”等八個固定套路,一個好端端的選拔人才制度,便異化成了鉗制人的思維乃至思想的工具。那名小朋友實際怎么想的、是不是逆反心理我們不知道,總之他可以“不讓”,套句時髦的話說,他有這個權(quán)利。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他何以“不讓”,倘若先武斷地判他錯了,便顯得相當粗暴。也可以說,這是對經(jīng)典沒有產(chǎn)生預期功效的一種本能反應,究其根本,正是把經(jīng)典的“尺度”功能絕對化了數(shù)控銑床。
上海一名小朋友在學完《孔融讓梨》課文之后答題,對“如果你是孔融,你會怎么做?”小朋友寫下了“我不會讓梨”五個字。結(jié)果,老師給打了個紅叉:錯。小朋友的家長對此不解,在他看來這道題沒有固定答案,“憑什么說真話就錯了呢?”于是在“一怒之下”把答卷曬上微博,請網(wǎng)友們評理。而網(wǎng)友在表達觀點之外,相關(guān)惡搞也接踵而至。對此,在下也不揣淺陋,說上幾句。
深層地看,“不讓”則“叉”,關(guān)聯(lián)我們的教育理念。
我們的教育理念,似乎像數(shù)控銑床工廠流水線一樣,但求制造出“標準化產(chǎn)品”,為此不可能容許兒童的“天馬行空”。曾經(jīng)讀到一篇文章,說美國內(nèi)華達州一名3歲的小女孩告訴媽媽,她認識“OPEN”中的“O”,然而母親在表揚了女兒之后,旋即把教她認識字母的那家幼兒園告上了法庭,理由是幼兒園剝奪了女兒的想象力。因為在認識“O”之前,女兒能把它說成是蘋果、太陽、足球、鳥蛋一類圓形的東西,而現(xiàn)在卻失去了這種能力。結(jié)果,幼兒園敗訴。在我們這里,此案例近乎天方夜譚,家長怕要感激幼兒園不盡。實際上,我們的前人也未必這樣塑造兒童。比如《世說新語》里有一則故事,“有人從長安來,元帝問洛下消息,潸然流涕”,這個時候晉明帝還只有幾歲,坐在爸爸的膝上,問他哭什么,元帝司馬睿“具以東渡意告之”——匈奴攻占晉都(西晉)洛陽之后又拿下長安,司馬睿不得不東逃建康重建晉朝(東晉)。有人從長安來,司馬睿自然觸“人”生情,但他就此給兒子提了個問題,你覺得長安和太陽哪個遠呢?小家伙答,太陽遠,因為“不聞人從日邊來”。第二天,元帝“集群臣宴會,告以此意”,再問一遍,不料這回小家伙說太陽近,因為“舉目見日,不見長安”。這個故事忝列《夙惠》,足見編者對小家伙能自圓其說的“出爾反爾”,持完全肯定的態(tài)度。
在現(xiàn)行的教育模式下,給“不讓梨”答案“打叉”的老師也不見得有什么過錯,他或她只是“教條教案”的忠實執(zhí)行者。“不讓”則“叉”,本質(zhì)上是教育理念在實踐中的一次具體投射。